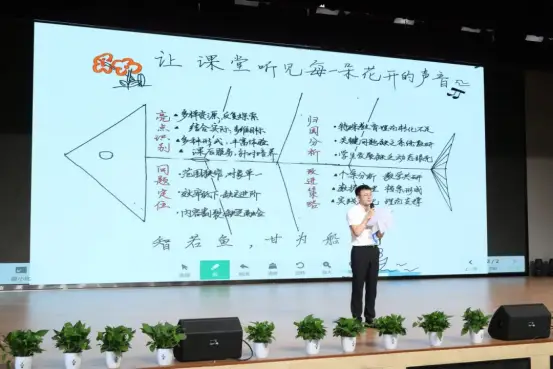三十里路外的小花开了
学校要求新接班级要加强家校沟通,尽快熟悉班级情况。家访是家校沟通最有效的途径之一。这一次,我前往小琳家。
小琳家在离校三十里外的偏僻山冲,妈妈在她出生半年后便离家未归,她和姐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是典型的留守儿童。这个女孩个子高挑,不善言辞,书写却很工整,但是偶尔会不完成作业。
去家访那天,我特意起了大早,骑着摩托车前往。一条水泥路弯弯绕绕,越往里走住户越稀疏。我中途好几次停车打听,得到的答复都是“还要往里走”。
快到的时候,远远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地坪里晒衣服。我刚停车,她就认出了我,惊喜地喊:“刘老师,您怎么来了?是来给妹妹家访的吧?妹妹跟奶奶去菜地了,快进来!”说着便搬来凳子,“老师您坐,要喝茶吗?我给您倒。”这是比小琳高一届的姐姐,我坐下和她闲聊起来。
过了一会儿,老太太骑着一辆带棚的女式摩托车回来了,后座挤着个小丫头,车斗里放着半袋刚摘的豆角。小琳直勾勾地盯着我,直到我喊她名字,才“呀”一声从车上蹦下来,脚刚沾地就往屋里跑。她奶奶异常激动:“老师来了!真的来了!快坐。这路太难走,让您受累了。”
我随她进了屋,陈设很简单:一张旧木桌,两条长凳,墙上贴着小琳和姐姐仅有的一张“劳动之星”奖状,边角都磨卷了。小琳一直站在门后,头埋得很低。我没提成绩,先指着奖状说:“这个‘劳动之星’评得真对,上次班里劳动课,小琳拔草最认真,还教同学分辨杂草呢。”她肩膀抖了抖,偷偷抬眼看了看我。
奶奶叹了口气:“这孩子命苦,生下来半年妈就走了,她爸在外打零工,一年回不来几趟。我嘴笨不会教,她就总闷着,在学校是不是也总躲着人?”
我摇摇头,拉过一把凳子示意小琳坐我旁边:“小琳不躲人,是我们没好好跟她聊天。上次她写《我的奶奶》,字里行间全是心疼,我在班上念的时候,好多同学都感动了。”小琳绞着衣角,小声说:“老师,我想学好语文,可我怕问错了被笑。”

“怎么会呢?”我看着她的眼睛,“老师小时候也总写错字,谁都有不会的,问出来才是聪明孩子。”那天我没讲大道理,就坐在长凳上,和她一起看课本插图,听她讲每天跟奶奶骑车上学的见闻,讲她和姐姐的日常。临走时,她递来一个小塑料袋,里面是自家晒的几颗杨梅:“老师,这是奶奶晒的,好吃!”
从那以后,小琳像换了个人。上课不再缩在角落,遇到不懂的题会红着脸举手:“老师,这道题我还是不会做。”我每次都耐心给她讲解,看着她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。期末语文考试,她从及格线冲到了八十多分,拿着卷子跑到办公室,声音不大却很清晰:“老师,我做到了!”
后来和她家人聊天时才知道,她常说:“刘老师每次温柔耐心的跟我说话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特别重要。”毕业那天,她抱着一小束带露水的野菊花站在教室门口:“老师,这是我早上在田埂上摘的。您是第一个到我家家访的老师,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。”
原来尊重从不是复杂的事,或许是认真听她说话的那几分钟,是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平等相待,是耐心倾听每一个孩子的诉说……三十里路的颠簸算什么?能让一朵怯生生的小花迎着光慢慢绽开,值了。
我会一直用这份公正与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,让更多“小花”开满山间,香飘四野。
(作者系浏阳市文家市镇里仁完全小学教师刘秀春)